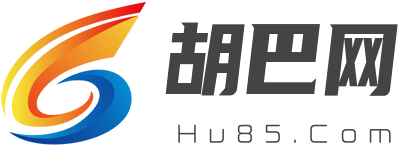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,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

文|《财经》记者 王雨娟
编辑|余乐
陈城城在上海一家投资机构做财务尽职调查,从他的位置看向老家,最容易嗅到的是传统行业的没落气息。
和许多“企二代”一样,陈城城中学起就被家里送到海外读书,拿到硕士学位后回国,讲话时会强调“中文不太好”,不小心蹦出英文词。只不过,对回家接班,他颇为犹豫。
陈城城家里的公司处于房地产的上游行业。下游市场的萎缩,导致行业里只剩下存量竞争。“以前是肉遍地都有,现在大家眼睛都盯着一块肉。”
谈起家里的公司,陈城城的语气充满担忧。在这个数字化已不再是新概念的当下,公司的业务还得倚靠大量的人力,标准化作业仍然是令人头痛的问题,现代化的办公方式也难觅踪影。
像陈城城一样的企二代还有很多:父辈的企业陷入转型困境,很多属于即将淘汰的落后产能。年轻的二代涉足其中,像一只误闯入黑森林的白兔。沉重的金汤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主体,家族企业占据企业总量的一半,GDP贡献超过60%。中国的家族企业涌现于上世纪90年代,很多一代企业家都到了必须“交棒”的时候。“新财富500富人榜”的数据显示,50岁以上民营企业家占比为67%——近七成的中国家族必须寻找接班人。
与此同时,中国的制造业也正面临转型的挑战,靠低附加值的产品打价格战、抢占市场的时期一去不复返。贸易冲突、经济增速减缓、国际局势动荡和疫情的影响更给民营企业的经营添加了诸多变数。这些因素都大大提高了二代们接班的难度。
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分享过一则关于二代接班的尴尬事。他受邀参加一位朋友的私人晚宴。席间还有八位企二代,都是清一色的80、90后,父辈则是1980年代开闯天下的草根创业家,从事的行业包括制造、地产或农产品加工业。吴晓波吃惊地发现,这些二代们要么在金融机构,要么独立创业,“居然没有一位在父亲的公司里就职。”
本文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群没有选择接班的企二代。我们试图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,寻找难以接班的原因。从他们的精神风貌中,也得以一窥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问题。
不敢接班,不愿接班
麦肯锡的一组统计数据足以说明传承的风险:全球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,仅有约30%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,能够传到第三代者不足总量的13%。只有5%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。“富不过三代”不仅仅是一句戏谑。
吴晓波曾因工作接触过许多二代。在他的观察中,这群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80、90后,有比父辈更优秀的视野、知识体系和价值观。他们绝不是垮掉的“坑爹族”。他们更乐于平衡工作与生活,懂得享受人生。
同时,他们遭遇的质疑和挑战也是父辈没有的,甚至是父辈无法体会到的。含着金汤匙出生,稍有不慎,那汤匙也压得人喘不上气。
程潇潇从小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。在家里的教育下,她对钱的概念早早就建立起来:吃下不喜欢但有营养的芹菜奖励200元,考100分奖励3000元,讨论课上主动做了组长则奖励更多——没什么不能用钱量化。
九岁时,表姑送给她七只毛绒公仔。在同龄小朋友还在给芭比换公主裙、涂口红时,母亲要她回答,如果带领七只公仔一起做作业,该怎么管理。
每一步都是家里安排好的。上国际学校,升高中时孤身飞到美国,大学读商科,再念个MBA。遇到长假期,母亲都会把她塞进公司里,“一个业务、一个业务地实习。”起初为了避嫌,程潇潇不冠父姓,后来实在去得太多,员工们也就心知肚明,“老板千金嘛。”
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,程潇潇第一眼就给人一种杀伐的气息,她的句子短促、有力,口头禅是:“你听我的。”
然而,真到程潇潇毕业了,接班却越来越不现实。不仅她没有信心,父亲也犹豫了。随着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昂,低附加值产品的工厂逐渐外迁向东南亚,而公司新的发展方向还未找到。这个产业,“连我这样的能人都搞不定了,更何况是你。”
这一担忧并非孤例。相较于从千军万马中人中杀出来的职业经理人,二代们少了重重筛选,能力上容易有缺失。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李海涛的研究表明: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,家族企业由父亲传给儿子,市值平均会跌一半。
欧洲与东南亚的许多家族企业历经多代接班,已有较成熟的机制,中国家族企业则无太多经验可循,多靠摸着石头过河。如果传承不力,父辈辛辛苦苦打拼的基业就可能付之东流。二代接班,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公众议题。
周运资同样是一位“不敢”接班的企二代。他出生于部队大院,家里是做房地产的。在家庭的熏陶下,他自小是孩子王,在同龄人中显得早熟,擅长交流,有感染力。经常他一说话,别人就觉得有道理。
但是,周运资坦言自己是地产的门外汉。多年来,公司内部运转已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架构。接了班,挂个副总裁的名头,插手后分到的钱反而可能变少,“别人很烦,还不如不管。”
除了能力,二代们欠缺的还有接班的意愿。老一代创业者为了企业能赌上一切,甚至不惜身体地赚钱。到了二代这里,创业的核心驱动力变成了兴趣,他们自小没有物欲匮乏的体验,创业也是能进则进,享受过程,但很难忍受艰辛。他们对待人生、事业和财富的态度,与父辈截然不同。
周运资父母的创业路靠得是一股狠劲儿。辞去安稳的体制内工作,离乡背井,失败了也不气馁,这才打拼下现在的家业。
到了周运资成长的年代,人们向往的是互联网和新能源造车。谈起这些高科技产业时,他的语气流露出羡慕,而回家接班一个地产企业,在他看来就是“开倒车”。
如今房地产市场的腾飞期已经结束,贷款收紧,行业巨头公司纷纷“暴雷”。家里的小公司摊子铺得不大,现金流暂时还能支撑住。他想得清楚,家里不提要求,他绝不会主动回去。毕竟一旦回去,不想做也没法走掉。除非有人找上来,否则绝不会多问公司一句,“分分钱就挺好。”
“哪天不行了就全卖掉,把钱存起来。”
尖锐的冲突
2015年发布的《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》显示,大多数二代并未明确愿意接班。其中,15%的二代表示不愿意接班,45%的二代对于接班的态度尚不明确。中欧商学院教授李秀娟表示,一半以上的中国传统民营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。
智慧云传媒创始人陈雪频将不愿接班的二代归为这几类:有的对父辈不满;有的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;有的养尊处优惯了,不想被约束;有的钟情虚拟经济,对于网络、电子商务、PE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,对创办实业、成本控制、精细化管理等兴趣不足;有的则选择留在国外,不愿回来。
过去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滋生出一个中国式问题: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,他们似乎都“别无选择”。父母只能把企业留给孩子,孩子则只能接父母的班——没有老二、老三可选。这让家族企业传承的矛盾更为尖锐。
中国第三家共享单车品牌——町町单车的创始人丁伟也是一位标准的企二代。他身形精瘦,说话时会微眯起眼,细长的脸不经意间左右轻晃。2013-2014年,他曾和父亲一起做互联网金融,向外放贷。这次短暂的接班尝试,以父亲将他逐出公司结束。
在做事的原则上,两个人截然不同。丁伟相信知识和眼力,肯花功夫自己做风险控制,身份信息、征信报告、银行流水,每一项都仔仔细细地检查过去。他只做小额贷款,一次最多5万。
父亲的贷款则主要面向经济开发区的老板。在丁伟看来,父亲看重人情,风控交给手下人,经常是几百万的单子大手一挥就批了,有人钻空子都未必能发现。
共事的半个月里,父子两个天天吵架。父亲已经答应放贷的人,丁伟怎么都不同意,“只要烂掉了一单,可能一年的利润都没了。”后来,父亲索性休战,私底下再悄悄把钱汇过去。吵也白吵。
在娃哈哈集团,女儿宗馥莉曾公开表示不赞同宗庆后的管理风格。面对中国生意场上难以避免的政商关系,父亲当作商业机会,宗馥莉直言不耐烦。这是很多家族企业二代的心声。
在东方式的父权至上家庭中,二代与父亲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。同时,企业的管理和决策又需要杀伐决断,代际矛盾很容易因此激化。
互联网金融之后,丁伟还和父亲有过一次权责更为明确的合作。2016年,正值国内共享单车的风口,丁伟与大学同学一起创立了町町单车。丁伟出任CEO,父亲则掌管财务。公司需要用钱时先要由父亲审批。
为了町町单车,家里前前后后投了一千多万。按照约定,除了投钱,父亲不会插手业务。但是,掌握财政大权的父亲从设计车款开始就不断提出不同意见,最终只能是丁伟妥协。
做到第三个月,单车资金链断裂。家里的金融公司发生挤兑,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,每天都有人上门讨债。
丁伟曾劝父亲变卖资产,填补5000万的资金窟窿。当时父亲的粮食厂房正面临拆迁,几十亩地一拆,是几个亿的巨款。“如果卖了工厂,这个难关肯定就过去了,但我爸舍不得低价出让资产。”
没等来拆迁,倒先等到了法院的强制执行,父母随之入狱。家里的工厂、房子和车子全部被低价拍卖。
尖锐的矛盾之下,消极的逃避便产生了。接班也很难施展才华,索性不如出走。
接班不易,创业更难
上述白皮书提到,有84%的企二代选择独立创业,或者在父辈的大盘中切出一块独立经营,以自证能力。但是,接班不易,创业似乎更难。
周运资刚上大学就开始折腾创业。他大学在湖北工程学院学国际贸易专业,在学校很积极,老师会私下教他写项目策划书,模拟创业过程。他是个急性子,晚上想着要干什么,可能第二天早上甚至半夜就开始了。
第一次创业时,他走出校门路过一家正在转让的奶茶店,周运资觉得“位置很好”,跟老板简单交谈过后就准备盘下来。
回到家,父亲仔细盘问了一圈客单价、开销、进货渠道、奶茶配方。这一问就把他问住了。但是,周运资急于求成,没想那么多。最终,父亲还是要了卡号,把钱打了过去,“就当交学费。”
结果不出父亲所料,坑一个接着一个。签完合同才发现房租快到期了,又补上房租。看似确实是每天客人不少,但是成本很高,租金、人工等开销一天近2500元。以客单价12元计算,一天得买200杯以上才能挣钱。营业额飘忽在1500-3000元,“有几个月到手是挣不到钱的。”
到了第二年交房租时,周运资已经不想做了,于是将店转让给朋友。“朋友跟我类似的家庭情况,说两句就接了。”最终,投资的100多万几乎赔光。
奶茶店的失败让周运资体会到实业的艰难,“赚的是辛苦钱,得慢慢积累起来,不适合急性人。”
大二下学期,周运资又转战金融类业务。他专门收集一些企业主的银行汇票,提前帮他们变现,等到期再去银行收回这笔钱。他从中赚取手续费。有时他上午收到票,不必等到银行汇款,下午就能卖给别人。资金周转很快,最大的风险是假票。两年后,由于这类业务政策吃紧,周运资没再当作主业做下去。
他的经历也表现出部分二代在创业中的共性:投机、离不开家里扶持、缺乏长期主义精神。
町町单车破产后,丁伟不得不找了份工作,在一家汽车整合服务公司任职,也做直播。借着共享单车还在热点,他靠直播赚了波快钱——三个月就差不多挣了六七十万。
采访时,丁伟刚开了家面馆,就在杭州师范大学门口。受疫情影响,学校叫停了外卖,面馆生意受到不小的打击。
但是,丁伟从不肯停止折腾,要么投资,要么创业,赔光了再接着上班挣钱,“很不安分。”即使没有继承实体公司,创业的基因也在他身上留下烙印。在社交网络上,他叫自己“追梦人”。
陈城城仍然准备暂缓接班。他还想再闯闯自己的事业,在光鲜亮丽的投资行业多待一段时间。另外,他认为接班的事情要到时机成熟才能和父亲谈。父亲没觉得到了干不动的时候,聊了反倒容易惹老爷子不高兴。
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家族企业教授罗晓薇认同这一点,家族传承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。企业业绩高于预期时,更容易顺利地传承。
传承也并非一簇而就,一个完整的过渡需要近10年才能走完。一代要放下英雄情结,接受老去的事实,腾出时间来慢慢放权,帮助二代的成长。
周运资的父母并不着急,希望他能慢慢地成长,到大公司里历练下,到一线城市看看,“体会下在自己家里永远都感觉不到的东西。”
但是,他还是打算继续折腾自己喜欢的。几次创业后,周运资转去慈善基金会当起了理事长,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读完初高中,每月工资1500块。在山里,他跟孩子们一样,每天吃土豆、穿布鞋、买50块钱的衣服。那带来很多成就感。他希望在公益事业上踏踏实实地做好。
毕竟——
如果不好好努力,就得回家继承家产。
(应受访者要求,周运资、陈城城、程潇潇为化名。杨赛对此文亦有帮助。)
本文来自零落投稿,不代表胡巴网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hu85.com/315981.html
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邮件至 xxxxx@qq.com 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