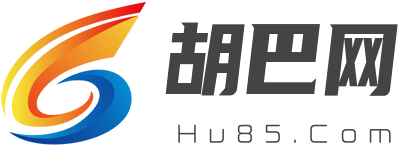爷爷去世二十周年祭
爷爷去世二十周年祭
时光飞逝,不知不觉爷爷离开 我们已经有二十年了,在爷爷去世十年的时候就想写一些东西,可是提起笔来却不知道要写些什么,从那着手,随着时光的流逝,记忆越来越模糊了,再不记起些什么,怕就要忘记干净了。

爷爷陈姓讳可观,宜城市王集镇中心村人,生于民国十四年冬月(爷爷说他的生日时就是这样说的),逝于2001年冬月,享年76岁。爷爷出生于贫寒家庭,我的太爷给好家的(地主,爷爷奶奶每每说起来就是说好家的)做活,太太(爷爷的妈妈,本地称太太)拉扯着爷爷和姑奶奶两个孩子,在村边上搭着一个草棚,就算是一个家了。我们这个家族同治年间有兄弟二人从江西搬过来以后,开枝散叶,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,已经有了约十几户了,那时候条件都差不多,除了一两家条件好点能住上房子外,基本上都住的草棚。爷爷说那时候一家子虽然清苦,但是太爷爷还是让他去上了私塾,这在我们那一族非常少的,所以虽然很苦,基本还是能生活下去,还有一些儿童时的快乐,但是简单幸福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。

民国二十四年(1935)的汉江大水淹没了整个村子,爷爷他们那一辈的人都说,天下塌了,平地起水一米多,他们一家四口侥幸的躲过了洪水,洪水过后,我的太爷爷却得了痢疾,那时候这个病是要命的,那一年爷爷不到十岁,姑奶奶七岁多吧,太爷爷去世后,实在没有办法,太太牵着爷爷和姑奶奶兄妹二人去讨饭,那时候都不富裕,经常饥一餐饱一顿的,还要忍受白眼以及恶狗的狂吠,吃些残渣剩羹更是家常便饭,后来太太给好家的帮工才勉强度日,就这样,后来太太还让爷爷上了几年私塾,成了当时营子(村)里有数的文化人,每当说起这些的时候,爷爷显的很随口的说出来,却又饱含着无比的伤感。

民国二十四年汉江大水片,来源于网络,涉侵权,请联系删除
爷爷二十岁时与我奶奶结婚,我奶奶大我爷爷两岁,有些亲戚关系,也算是门当户对,都是亲家子巴业的。他们一生养育了六个子女,四儿两女,在当时的条件下,养活六个孩子是多么的艰难,于是爷爷除了基本的农活外,还学会了砌匠、木匠、篾匠、磨匠等手艺,外面有活帮忙,没活的时候就在家里编竹筐、做小凳,以换取一些钱粮来养活一家人。六几年不让市场自由买卖时,爷爷一个人偷偷跑到山里端了一年多的石磨,挣了两百多元,把我的父母的婚事给定了,但由于吸入石屑过多,落下了尘肺病病根。六十年代末,我母亲去相亲的时候,爷爷把我的叔和姑都赶出去了,不让在家,因为他们穿着实在不敢让人恭维,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,老二穿了老三穿,补丁摞补丁。怕我母亲看了后相不中,好在我母亲终于还是嫁给了我父亲,才有了今天这篇回忆。我想大抵一点主要是沾亲带故,我母亲的姨奶奶和我奶奶娘家一个姑是表亲,不好驳面,那时候人对人情还是很在意的,放在现在肯定是成不了的。二是我父亲是一个很真诚的人,后来听我母亲说,要不是看你老实本份,肯定不会找你。一辈有一辈的想法,现在太本份的人是不行了。

我母亲嫁过去的时候,爷爷通过努力,家里有了三间小瓦房的正屋和两间草房的厨房,正房地脚用了六七层的青砖,青砖上面是土坯砖砌成的,外墙用泥巴夹着稻草糊的墙面,厨房的四面墙全部用土坯砖砌就。这里面住着三代九口人,我的父母成婚后,占去了一间,就显得更加拥挤了,所以我的叔和姑他们就轮流在关系好的邻居或同学家借住,虽然我的太太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去世了,但是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分家。
说实话,童年时对爷爷的印象并不是很深,只是在分家的时候我才关注过一下,因为那一天在我来说太奇怪了。大约在我七八岁的时候,有一天,家里的坛坛罐罐全部摆在了院子里,并且请来了我的舅爷,大家站在院子里指指点点,嘴里说着什么,成人后我才知道那是在分家。
分家后我和母亲搬离了祖屋,在其他地方重新盖起了土坯的房子,从此,跟爷爷、奶奶他们见面了机会便少了。说起来爷爷在我的童年还是有让我骄傲的地方,那应该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,小队(现在的组)里办育红班(幼儿园),爷爷给我们泥的黑板,并教会了我们认识算盘和珠算基础,小伙伴们都很羡慕我,着实让我风光了一回。
爷爷是精明的,也是勤俭的,也许小时候穷怕了,显得特别节约,甚至到了扣的地步。他要求他的子女们在吃饭的时候,必须把碗里添干净,不然就是一筷子就敲到了头上,吃稀饭馒头的时候,必须先喝稀饭,然后才能吃馒头,这样容易有饱腹感,如果先吃馒头再吃稀饭,在爷爷看来,稀饭就浪费了。爷爷的精明我只是听说,但我知道的显示在分田到户上,那时候盘点小队的资产,除按劳动力分田外,包括牛、马、猪、农具等所有的集体资产都作价,然后进行搭配由社员(村民)选择。当时小队里有一匹瞎马,已经怀了马驹,作为小队会计的爷爷心里十分清楚,作价的时候作得较高,这样就没有人选,别人不要,就落到了他的头上,颇有些《暴风骤雨》中“老孙头”选马的风范。这匹瞎马半年后下了一只小马驹,爷爷很是开心了一把。那匹瞎马我还曾多次牵到汉江堤上放牧,有一次在王集镇三洲村一不小心摔倒在了路旁的菜园里,当时十二三岁的我急得直哭,手足无措,还好村里的几个年轻小伙帮了我的忙,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放牧过那匹瞎马了,后来回到爷爷家没有见到那匹瞎马,也没有问过,现在想到还有些遗憾。
爷爷他们那一辈人总是闲不住的,也是非常劳苦的,他后来总跟我们说,过去时候才是真的苦,真的穷,所以为了多挣点,多跑点路,多出点力都无所谓。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83年,那时候爷爷已经58岁了,为了多挣几个钱,爷爷自己在家做了几百斤粉条,早上五点多钟就起床了,在家里装在板车上,从王集中心的家里向孔湾镇上出发。那时候宜城汉江大桥还没有通车,过汉江还要坐渡船。爷爷就这样一人一板车,拉着一车的粉条在当天下午五点多钟到了孔湾镇街上,路上馒头就着汉江水解决了中饭。,只因为孔湾街上的粉条比王集的贵一毛钱,能多卖个二三十元钱爷爷硬是拉着几百斤重的物品走了七八十里路。在孔湾卖完粉条后,又一人一板车回到家里,当时我无法想象,现在感觉更加不可思议了。
为了能让自己的日子过好点,不多给子女添麻烦,爷爷奶奶在田里的功夫也没少下,并且为了耕地,还养了一头牛,为了防止牛被偷走,他把牛养在自己卧室的窗户边。这样,只要有一点响动,他们就会惊醒,虽然牛养得很好,也没有被盗,可是住的地方气味自然是很难闻的了,并且跳蚤比较多,可爷爷他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,只是一心一意的去侍弄他们的牛。好的耕耘就会有好的收获,爷爷种的田年年丰收,生活向前,日子渐渐好转,记得爷爷第一次种出了自己田里的稻谷,他打成了米给一个子女送了一点,说终于有了自己的田,吃到自己种的米,可惜的是我的老家那里是沙土田,蓄不住水,后来全部改成了旱田,再也没吃到爷爷亲手种的大米了。
随着日子的好转,爷爷年岁的增长,也有了时间来享受一下人生了。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、听戏、抽烟、打牌,我记得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,我给他买过两本书,一本是《呼家将》,一本是《薜刚反唐》,每本有三四百页,过了约一年多的时间,我发现那两本书既然被翻烂了一些,可见看了多少遍了。爷爷有一台“红灯”牌收音机,那可是他的宝贝,一般是不让别人碰的,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就会打开他的宝贝,嘴里叼着旱烟,听着“说书”节目。从我记事起就看着爷爷抽烟,当然不是现在的纸烟,而是自己种的生烟叶,他每年都会拿出两分地来种植烟叶,然后自己晒干,自己收藏,自己揉碎,自己把烟叶装烟袋里,自己装烟锅里,自己点燃,自己享受,我曾见过爷爷有两枝烟杆,一枝有一米多长,一枝约二十多公分,他对烟草的喜爱如同他对打牌的喜爱一样,终于对他的健康造成了影响。日子好转,有了闲暇,爷爷也和他差不多年岁的村里的老人玩,平时玩一下,白天玩一下对身心都是人好处的,可是爷爷六七十岁的人,还常常熬夜,为此,我父亲做为长子联同我的叔和姑不知道劝了多少次,效果都不大,终于有一次感冒后引发了肺部感染而去世。

爷爷奶奶对于我来说,是千万般的语言也叙述不完的,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,是一辈只管一辈的事,抚养和赡养都是对儿辈和子辈,对孙辈是没有业务的,这也是动物的本性和应该遵守的规律,但是做为感情动物,我们又有一句话叫“隔辈亲”。那爷爷和奶奶对我的孩子就更亲了,也是,老大的老大的老大,爷爷奶奶显得更加亲热一些。那是我孩子七八个月的时候,我和妻子要上班,一时请不到照看的人,爷爷奶奶便自告奋勇,要替我们照顾孩子。考虑到爷爷奶奶已经七十岁高龄,有些犹豫,但是爷爷奶奶爱重孙心切,又疼他的孙子、孙媳妇,果断决定要帮我。为了爷爷和奶奶的晚年,在得到了我的父母同意后,我和妻子又征得了三个叔叔和两个姑姑的同意,这样七十岁的奶奶和六十八岁的爷爷便离开了家乡,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。他们来的时候,身体还是很好的,我的妻子也经常到街上买一些食材和时令的熟菜,然后他们两人推着他们的重孙子在大道上走着,并对他人自豪的说,这是我的重孙子。很是惹得了人们的羡慕,有了很多的话题,不到一个月,便跟周边的人很熟络了,并且遇到了我太太家的侄儿,也就是我爷爷的亲老表,只从我太太1970年过世后,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,几十年后偶遇,让他们两人都很高兴,互相窜着门子,隔三差五的一起聚一聚,加上我的母亲和两个姑姑经常来看看他们,爷爷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,很是让人开心。但是,我真的不想用但是,但是还是发生了,由于我没有很好劝说的原因,让爷爷的老毛病复发了。虽然我的父亲和几个叔叔和姑姑没有怪我的意思,爷爷的早逝我还是很内疚。
我所工作的地方离火车站不远,那时候火车站有一个很大的货物转运站,又是开放式管理,吞吐量很大,特别是煤和粮食比较多,转运的车辆也不是很规范,什么样的车都有,这样洒落的机遇比较大,洒落的货物也比较多,附近的老人们经常拿着扫帚和口袋在路上清扫洒落下来的货物。爷爷不知道从哪得到的信息,听取了谁的建议,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第一天竟然扫了四五十斤煤,当时的煤价大约是四百元一吨,人均工资大约120元左右,对于种了一辈子田的爷爷来说,简直跟捡钱一样,乐此不彼。由于路上清扫货物的老人比较多,要看谁的动作快,所以爷爷还要和他们比动作,一般扫了几斤后就得放回去,不然,货场的人会来清收,虽然管理不是很严,毕竟还要管理,爷爷就这样一天往返数次,路程倒不是很远,可是年龄在那,我也多次劝过爷爷,别那么拼,又不差那点东西和钱,可是爷爷是听不进去的,几个月过去后,看着门前的煤堆从几十斤一个小堆变成了好几吨的一个大堆,家里的几个空了的口袋里面又装满了玉米、小麦、稻谷等各种各样的粮食和用粮食换来的几十斤的酒,爷爷很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,这对于一个老农民来说,是不可想象的,还常跟我说:“要是再年轻点,在这里能扫不少钱。”他完全不顾他有肺病的实际,我让我的父亲和几个叔、姑劝他,可是一点效果也不见,终于在半年后一天旧病复发。虽然经过治疗,病情得到了控制,但是已经不能再做重点的体力活了,本来消瘦的身子更加消瘦了。我的父亲和几个叔姑商量后,带着一车的煤和各种粮食把爷爷奶奶送回了老家。出于对爷爷奶奶的感恩和感激之情,我基本每月都要回老家几次,每次都买上一些鱼、肉、米之类地去看望他们,有时候留下一些小钱,只能尽点心意罢了。
爷爷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,奶奶离开也有快十年了,坟上的青松已经由指粗长到碗口粗了,几十年的相处岁月,很多往事涌上了心头,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只能简单的回忆一些小事以示对爷爷逝去二十年的一点祭奠吧。

本文来自零落投稿,不代表胡巴网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hu85.com/256762.html
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邮件至 xxxxx@qq.com 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