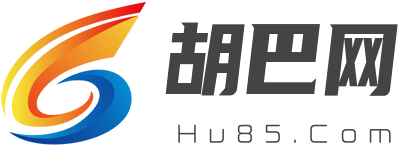吴绪昌面色凝重,沉吟片刻招手将何栖云叫了过来:“把金梭子拿过来。”何栖云忙走到他坐骑边,从马褡子中取出一个小小布包来,打开布包里面却有九根金灿灿的物什,都是一般大小,两端皆细锐如针,只是中段略粗。吴绪昌小指一勾,五根金梭子自动跃到了他手中。他平摊左掌,右手捻住一根金梭子,快速地钉在杜老憨的顶心百会穴上,接着又取了两根,分别扎在他左右掌心的劳宫穴上,最后两根他左右施为,同时扎入杜老憨脚心的涌泉穴上。吴绪昌将金梭子钉进去之后,又嘴唇翕动,念了一段谁也听不清的咒语,半晌方才停住,缓缓站起身来。
镇八方还没开口,急脾气的炮头崔大力早就忍耐不住,张口问道:“怎样?”吴绪昌道:“这是山间邪物作祟,我已用金梭子镇住他五心,只消过得七个时辰,然后再下葬就没什么事了。”崔大力虽然和他同在山寨多年,知道他除了精通诸般阴阳术数外还有一手镇邪去祟的本事,但也是第一次见他施用,不由又提出一个问题:“金梭子不是有九个吗?为什么你只用了五个?”吴绪昌微微一哂:“九个全用那是经天纬地燮理阴阳,只有真龙天子才当得起,就是七个那也得是王侯将相,照例说杜老憨在山里也没啥贡献,只用三个布成三才阵也就足够了,用五个已经是多了。”他说着扭过头对镇八方说道:“大掌柜,杜老憨的尸身需要静置七个时辰,我们不能赶夜路了。”镇八方也知道吴绪昌句句属实,便叫孟仲义带几个土匪选落点。
本来这荒山野岭的没啥地方能躲避风寒,但孟仲义他们去了不消一柱香的时间,便派了个小匪回转来:“大掌柜,那面有老木扒留下来的柴禾棚子,可以先歇一歇。”镇八方一挥手:“走,到那里落脚!”众土匪便随着那小匪前行,内中有两人专门抬着杜老憨,走不多远果然在一个避风的旮旯里找见了几间柴禾棚子,它全是用砍成对半的原木一层层搭起来的,连头顶也是如此,为了方便进出,压根就没有门的设置,那个位置是空着的。不消说,这是山里伐木的工人不便下山休息而搭的临时休息场所,虽然简陋不堪,但总好多在外面忍饥受冻。
粮台黄山屏先派人收拾出一片地方,又不知从哪鼓捣出一堆干燥的稻草铺在地上,请镇八方和几个掌柜先过去休息,接着又命人去四周划拉些烧柴,准备架火取暖,顺便做点吃的。土匪人数虽多,但那几间柴禾棚子也真够大,众人在其中倒也不觉得十分拥挤。在吴绪昌的指挥下,杜老憨和其他几位睡了的兄弟被抬到棚子的西侧。吴绪昌不放心这些粗手笨脚的土匪,当他们放下尸体后他又亲自查看了一番,见五枚金梭子还都牢牢地钉在原位,这才放心回去和诸位掌柜坐在一处。
不多时砍柴的土匪也回来了,人人抱着一大堆新砍的木柴。东边道的山上遍地都是尚未开采的原始森林,要劈点柴禾易如反掌,尤其是冬天的树木都被冻得脆生生的,拿刀一砍那些枝枝丫丫就自己掉下来了。虽然新鲜木头含水分多并不好烧,但土匪们常年在外漂泊,几乎人人都是野外生存行家,不消片刻一堆堆热乎乎的火苗就升腾起来了。他们将雪水融化,就这随身携带的干粮啃上两口也就算对付了一顿。不过像镇八方这种大掌柜除了普通干粮之外,还能吃上几块香喷喷的狍子肉干——这都是土匪平时在山里打的,不过毕竟数量有限,除了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大伙能敞开肚皮吃一顿外,平时也就几个掌柜有这个口福,普通土匪基本上是有啥吃啥,比如下山抢到了鸡就吃鸡,牵来了猪就吃猪,虽说比山下普通百姓吃得要好,但和山寨中的头领肯定是没法比。镇八方吃完饭,反手用袖子抹了一把油汪汪的嘴唇,粗着嗓子道:“巡风的把招子都放亮点,其他人都地上拐着。”土匪们经过了白天的激烈战斗,此时也是身心俱疲,他们头朝内脚朝外,歪在地上裹紧棉袄,不多时鼾声就响成了一片。

何栖云挨着吴绪昌躺下,脑中仍然想着匣子的事,半天无法安睡。他在地上翻了下身子,却正好和吴绪昌相对,吴绪昌正睁着双眼,显然也是腹有心事。他悄声道:“先生,你也没睡?”吴绪昌冲他挤了挤眼睛,示意他稍安勿躁。何栖云会意,不再胡乱动作,又待了约有小半个时辰,众土匪的鼾声此起彼伏,显然人人都睡得极沉。吴绪昌轻轻从地上支起半个身子,见四周并无异样,用脚尖踢了何栖云一下,何栖云随即站起身来,跟着吴绪昌走到了角落的一处火堆旁。这儿离众土匪都有些距离,轻声交谈他们是听不见的。
何栖云心中藏着太多疑问,不过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,他把匣子塞到吴绪昌手里,吴绪昌轻声道:“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有这东西的,嗯,它名叫太初玄武鼎,内中隐含了三百年来的一个大秘密,我就从它的来历说起吧。”
“凡是历朝历代,皆与五行相应,后代灭前朝,即是五行相胜。五德终始,循环无端,如汉朝、宋朝、明朝都是火德,克制明朝的清朝便是水德。清以水立本,不仅起家于东北苦寒之地,从地理上说占了一个水,连国号中也有水,而原来的国号金又是生水的。攻灭明的那一年,是崇祯十七年,也是黄帝以来第七十三步大运的甲申年,那一年该着明朝灭亡,元、会、运、世四爻皆在陷地,甲申的干支纳音又是泉中水,这诸水相加,明朝国运焉能不败!”
“龙兴必有其地,这清朝的龙脉便是起于我们脚下的长白山。这座山古称不咸山,它横亘辽东,绵延三千多里,是昆仑祖山东出三龙之中北龙的尽头所在。七十三步大运当六白武曲,朱家的南龙已败,北龙当兴。当时有不少士大夫心伤故国,矢志反清,内中有一位精通风水的大师,即世称地仙的蒋大鸿。蒋大鸿虽然术法通神,但对弟子总是遮遮掩掩,不肯讲真口诀尽行泄露。只有一名弟子因为父母被清军诛戮,发誓要报得此仇。蒋大鸿见他心坚如铁,遂将自己平生所学青囊以传。这名弟子出师之后,便秘密来到了辽东,准备以一己之力毁掉龙脉。而其时清朝已定鼎中原,对起家的龙脉倍加珍视,为防止有人恶意毁伤,在辽东筑起了一道南北数千里的边墙,并委派专人巡守,不许任何人入内打猎砍柴挖药材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‘柳条边’。那名弟子来到辽东后,装扮成一名乞丐,趁看守兵丁不备混进了长白深山。他一路餐风露宿,观星寻龙打探结穴所在,终于找到了真龙落脉之所。虽然此龙过峡束咽不合窝钳乳突四大穴法,但他从撼龙关窍入手,靠着自己出神入化的峦头理气本事,终于准确地察觉到龙首所在,并在上方打下一口金井,找到了五色土之上裁玉切肪的龙脑,将它取出来藏在自己专门为此打造的盒子里,这就是太初玄武鼎的来历。太初者,事之初也。古人谓太极为道之极,太玄为道之玄,太素为色之本,太一为数之始。此物为混沌未蒙而开,故用太初为名。玄武是北方正神,乃龟蛇共生,合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七宿,因此龙是水龙,所以引用玄武之称。至于这盒子为什么称作鼎,是因为龙脑乃是活物,虽然脱离了本体仍可存活,而这盒子犹如丹炉一样熔冶龙脑,所以就被叫做鼎。其实鼎也未必是有形有质的,比如练习吐纳功夫的人,丹田即可作鼎修化内丹。”
虽然吴绪昌说得很详细,何栖云仍是未能明了:“既然这位前辈已经取走了龙脑,那清朝国运怎么又绵延了三百年?不是应该即时中绝才对吗?”吴绪昌神情一黯:“这龙脑是真的不假,可事实上水龙的龙脉却有两条,一条阳龙按河图五子运以丙子水龙透出地表,四外罗城拱卫,前有案朝之山,左右有颔首龙、平洋龙层层守护,穴下结有唇毡,但力量并不大,真正起作用的却是那条不循常理的阴龙。这阴龙和阳龙系出同源,但所行山川河流和阳龙并非一路,龙脑所在更非常人得见。本来阴阳相辅相成,该是一个三元不败的大地,要走行三个三元也就是五百四十年才会入囚,若是阴阳龙都被破掉,那就毫无问题,但若只破阳龙,阴龙靠着强大的实力仍可保住至少一半的年运,因此那位前辈虽然取走了阳龙的龙脑,清朝却仍是得了二百九十五年的国运。”
何栖云又抛出一个新问题:“这纪家虽说在浑水县有些势力,可也并非前朝皇族,说不好听的就是个土鳖财主,他们家怎么会有这么珍贵的东西?”吴绪昌摇摇头:“这我也不明白,不过只怕他们家也不了解龙脑的妙用。我是白天在院外望气,见到纪家冒出一股黑死之气又现出三道金芒方才得知的。纪家有黑死之气并不奇怪,东边道的这几个绺子一起典鞭,少说也有四五百号人,凭纪家的那点儿人马怎么会是对手,迟早要去拜见西天佛祖。这三道金芒却大大不一般,道家始祖老子一气化三清,只有混沌未开的神物才会有如此光芒,所以当时我才叫你去找,没想到还真在那里。”
何栖云有些担心地问道:“可是它并非我先发现的,今天最先看到它的是张大轱辘和杜老憨。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开看过了,而且他们看完之后就脸色煞白,像是活见鬼一般,我问什么他们也不说,而晚上杜老憨就死了,这两件事是不是有所关联?”吴绪昌脸色一变:“他们看过了?唉,这阴阳龙脑若不是集在一处,是万万不能打开的呀!”说着他急匆匆地站起身:“快去看看杜老憨的尸倒!”他这么一说何栖云也悚然惊动,两个人快步奔向停放杜老憨尸体的地方。
杜老憨的尸体虽然还停放在原处,但两人走近一瞧不禁大吃一惊。杜老憨全身上下不知何时起了一层细密的绒毛,那绒毛生得密密麻麻,远远瞧去乌蒙蒙的,便如快要放坏了的杂合面窝头一样。尤其是胸口有手印的位置,现在绒毛已经长到一指多厚,看起来比别的地方长得迅速得多。而杜老憨紧闭的双眼皮上,还长出了两圈淡红色的晕轮,和月晕有几分相似,乍一望去像是睁开了眼睛。而吴绪昌钉在他五心的金梭子,顶心的那一枚已经跌落到了一旁,其他四枚也是摇摇欲坠。何栖云心口突突直跳,只觉口干舌燥,紧张的连话也说不出来。吴绪昌捏了一个剑指,口中默念两声咒语,骈指戳在杜老憨的两胁之上。杜老憨忽地张开嘴巴,口中吐出一道黑气,如烟柱般直扑吴绪昌而来。吴绪昌却是早有准备,他咬破舌尖大喝一声,宛似平地里响了一声春雷,一口鲜血早喷在杜老憨脸上。杜老憨下颌关节喀喀作响,张开的嘴巴又缓缓合上了,那身上的一层绒毛也随之萎缩,眨眼间已尽数脱落,到了地上后很快便和泥土混在一处,再也分不清彼此。吴绪昌重又将顶心的金梭子钉了回去,轻轻地吁了口气。
吴绪昌的这一声大喝却将土匪们都惊醒了,他们紧张地从地上跳起来,四顾之下并没有旁人,只有吴绪昌和何栖云站在杜老憨尸体旁边。镇八方披着大衣走了过来:“先生,出什么事了?”吴绪昌指着杜老憨的尸首道:“刚才发生尸变了,幸而我已用五雷正心法将其镇住,现在已经没事了。”这时守夜的两个土匪也从外面慌里慌张地钻了进来,镇八方冲他们挥挥手:“大伙儿却继续眯着,妈了个巴子的,这杜老憨真是麻烦,大半夜的也不消停。”众土匪见并没有什么异常,于是一个个又躺回原位,继续梦会周公去了。
何栖云跟在吴绪昌旁边,眼见吴绪昌虽然破了尸变,却仍是眉头紧锁,不见半分轻松,便开口问道:“先生,可是有什么不对?”吴绪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叹道:“杜老憨这是招来了罗天煞,我现在也只能将其驱走,而不能阻止它在这附近盘桓。更麻烦的是,这次事情不会如此轻易了结,三天之内绺子里还会发生别的事。”何栖云问会是什么事,吴绪昌说道:“这我却也不知。龙脑见了天光,引来的神煞皆不在六爻通变之内,无法推演出来。唉,我让你取太初玄武鼎,也不知是福是祸,现在也只有见招拆招了。”何栖云心下惴惴,却又不敢多言,只能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躺下。
这时节已过了二更天,外面山风一阵紧似一阵,呜呜咽咽地如泣似诉,何栖云听着山风呼啸,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。
次日早上何栖云是在土匪的喊叫和喧闹声中惊醒的。他揉揉惺忪的睡眼,看见几个大头领正围坐在一起,镇八方、吴绪昌、孟仲义、李四宝等都在内,人人面色凝重,显见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。其他人这时虽然显得稍稍安静了一些,但也都是面现惊慌之色。何栖云拉住身旁一个土匪,小声问发生什么事了,那人说道:“张大轱辘今早了水的时候被冻死了。”何栖云脑子“轰”地一声响,一时竟然呆住了。恍惚间他走出门去,看到门口两三个土匪正指着地上一具尸首小声议论。那尸体穿着土布棉袄,耳朵后面别着一杆烟枪,一双大脚板上的趟土子活像两只小船,却不是张大轱辘是谁?他整张脸都被冻得青紫,一张豁风嘴斜斜咧开,两排黄白色的板牙向外呲出,颧骨下两块肌肉微微隆起,这表情丝毫不像遭受什么痛苦,分明就是在笑。只是看他冻得僵硬的身体,却一定死了有一段时光了。
何栖云从土匪们只言片语的议论中慢慢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。昨晚上水香孟仲义和以往一样,安排了一小队土匪巡风值夜。土匪们值夜都是换班,每两人为一组,一次在外面也就是一柱香的时间,这也是为什么山寨里负责侦查放风的头领被叫做水香的原因。之所以时间这么短,一方面是为了让土匪保持警醒状态,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有时间进屋烤火取暖,不致被严寒冻伤。张大轱辘被排在了昨晚这一队土匪之中,轮到他和另一个土匪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。一柱香的时间并不长,再加上外面奇寒彻骨,了水的两人谁都没有开口说话。差不多到时间的时候,另外两个土匪出来接替,和张大轱辘同班的土匪喊他回去,张大轱辘没吱声。新来的两个土匪中有人说道:“轱辘愿意在外面就让他再值一班,我先回去眯一会儿。”就这样只有一个土匪顶在了外面,而再到换班的时候又有人偷懒,谁也没认为这个朴实的庄稼汉子能有啥意外。
可是等到天色渐渐转明,终于有人发现张大轱辘不对劲,他始终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,连手都不抬一下。要知道在这样寒冷的环境中为了保持身体的温度,人们都会不间断地搓手跺脚,哪有呆立不动的道理?那人喊过几声,见张大轱辘没反应就大着胆子上前推了一把,不料张大轱辘应手便倒,再仔细一看人都死透了,这才扯着嗓子喊了出来。
张大轱辘死得蹊跷。镇八方已经派人查验过,张大轱辘身上并无伤痕,看脸上笑的表情就是被生生冻死的。可他是土生土长的东边道人,活了三四十年了什么样的冷天气没有见过,防寒的顶天(帽子)、棉手焖子、趟土子一样不少,再加上昨晚是阴天,外面压根就不是最冷的天气,就是一个半大孩子也冻不死,怎么可能会冻死这个身强力壮的老杆子?本来昨天杜老憨就死得不明不白,再加上他这一死,众人心里就更加难以平静了。
而何栖云在他们的担心之外,更多了一层隐忧,昨天发现太初玄武鼎的两个人,才不到一天工夫就都离奇毙命,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,而是来自一种神秘力量的支配,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,却是谁都难以预料。
本文来自残念投稿,不代表胡巴网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hu85.com/205245.html
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邮件至 xxxxx@qq.com 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