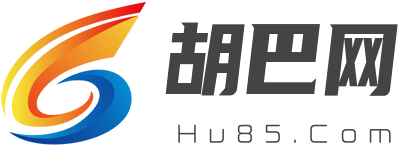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,
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——题记
2017年4月,一则新闻让喜欢老上海情调的粉丝们激动不已——经历了85年的风风雨雨,那个曾经让无数上海人神往的百乐门舞厅重新开门迎客。
“月明星稀,灯光如练;何处寄足,高楼广寒;非敢作遨游之梦,吾爱此天上人间。”
这是当时一位不知名的文人写下的百乐门极盛时期的景象。
十里洋场,红男绿女,香鬓丽影,轻歌曼舞间多少爱恨痴嗔,几多离人别怨,都化作了上海百乐门门庭上那抹最绚烂的霓虹——闪耀却最终归于沉寂……
但那些故事,那些人,真的就如黄浦江中那个不经意的浪花般湮没了吗?
白先勇先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。
在他的小说集《台北人》中,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到退了休的女仆顺恩嫂,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,从知识分子到帮佣工人,从军阀到歌女,三教九流,各有各的境遇,各有各的心酸,却又“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。”
而这其中,金大班是一个绝对不能被忽视的角色。
她,风尘浪荡,她,仗义助人,她爱的浓烈,恨得决绝,她精明世故也执着烂漫,她是百乐门里最耀眼的“玉观音”,也是碾压成泥的“死不得”……
这是她的故事,难忘,难堪,光彩照人又悲戚哀伤,你听,歌舞声响起,嘘,金大班来了……
踩不完恼人的舞步,喝不尽醉人醇酒良宵有谁为我留?耳边语轻柔
华灯初上,台北夜巴黎舞台,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印在楼梯上,好听而悦耳,但这声音听在总经理痛得怀耳朵却又如针刺又如蒙大赦,他窜出来,囔道:
“金大班,你们一餐饭下来,天都快亮喽。客人们等不住,有几位早就走了!”
金大班本想打发两句,却不料痛得怀犹自不停地埋怨着。
“金大班听见了这话,且在舞厅门口刹住了脚,让那群叽叽呱呱的舞娘鱼贯而入走进了舞厅后,她才一只手撑在了门柱上,把她那只鳄鱼皮皮包往肩上一搭,一眼便睨住了童经理,脸上是似笑非笑地开言道:……夜巴黎不靠我玉观音金兆丽这块老牌子,就撑得起这个场面了?……天天报到的这起大头里,少说也有一半是我的老相识,人家来夜巴黎花钞票,倒是捧你童某人的场来了呢?……我金兆丽在上海百乐门下海的时候,只怕你童某人连舞厅门槛都没跨过呢!”
一席话连珠炮似的,句句在理,字字有声,嬉笑怒骂却又有理有据,刺的人生疼却又找不出做声的理由。
金大班,这个倍尝人间苦辣酸甜,在风月场中摸爬滚打二十年的高级舞女立刻跃然纸上。
她阅尽沧桑,作为一个“货腰娘”,她整天被人家搂腰摸屁股,受那些“又脏又臭”的男人们的窝囊气;
她争强好胜,尽管最后只能落得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的结局,仍不忘刻薄丁香美人任黛黛“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”;
她看透世事,玩转情场,她是“九天妖女白虎星转世,来到黄浦江滩头妖乱人间的精灵”;
她也是“哪个大头耍的多,耍的狠,耍的漂亮”的头牌舞女;
还是那个一边骂“被人搞大了肚子”的小舞女,一边又甩下“一克拉半大油大钻石戒指”的仗义大姐。
她不是任何人,她的经历,她的风光,她的苦楚,只决定了她只能是金兆丽,独一无二的金大班。
她就像一个复杂的器物,让人看得见却摸不清,让人沉思,也令人迷惘,她的复杂来自于她经历的丰富与深邃。
这样的人物,无关好坏,无论短长。
二十年的舞女生涯,她在在苦痛中寻乐,在寻乐里沉沦:她在抓人大头中寻找乐趣,利用姿色搞的人家妻离子散,你以为她快乐,却也分明感到她的苦楚,她被男人当做“玩物”,被家人压榨;她在胜利中失败,在失败中又饱尝快乐,她骗得棉纱大王潘老头打得金山一座,又一脚踢给任黛黛,她胜的漂亮;但看到任黛黛坐在自己丈夫的绸缎庄摇着芭蕉扇,她却也败的“牙痒痒”。
她为月如付出过真心,也辜负过秦雄真意,她笑话人家“饿嫁”,却也为了下嫁陈发荣“下足了功夫”,她真心实意,也市涉世俗,她说:
“四十岁的女人不能等,四十岁的女人没有工夫谈恋爱,四十岁的女人——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。”
快乐或痛苦,失败或胜利,真诚或虚假,矛盾如百乐门里的七彩霓虹,炫目而复杂,但或许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有特质。
因为人生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游戏,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在晦涩不明的灰色地带游走,有过片刻真心,有过几缕恶意,走过喜悦,也路过悲伤,你若没有七十二变,怎经得住这残酷的九九八十难?
走不完红男绿女,看不尽人海沉浮,往事有谁为我数?空对华灯愁
这是金大班二十年舞女生涯的最后一夜,明天她即将嫁给那个小橡胶厂厂长陈发荣。
二十年来,她用年轻、漂亮作为资本,漂泊在一个又一个男人的怀抱,从上海的百乐门的红极一时到台北夜巴黎的昨日黄花,她像一根没有根的浮萍,暂时停留,却无处容身。
作为一个“在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滚”的女人,她太懂要在这些红男绿女中间得一分真心的艰难,于是她痛骂朱凤:
“玩是玩,耍是耍,货腰娘第一大忌是让人家睡大肚皮。舞客里哪个不是狼心狗肺?”
劈头盖脸,不留情面,金大班骂地狠,也骂地痛,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朱凤的对爱情的幻想,可那份幻想何尝不是她自己的?
曾经她是那么爱着月如,爱得如痴如醉,是真挚,动情的,她不是不知道欢场情薄,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——“她和许多男人同过床,每次她都偏过头去,把眼睛紧紧闭上。”而与月如,她则:
“一刹那,她觉得她在别的男人身上所受的玷辱和亵渎,都随着她的泪水流走了一般”……
当姆妈和阿哥联合起来狠心地将那个已经成型的男胎打落,刚强如她,市场如她,精明如她,也第一次萌了短见:
“吞金、上吊,吃老鼠药,跳苏州河——偏他娘的,总也死不去。”
那一刻的绝望是为了月如吗?是为了那个孩子吗?
可能都有,可能又不全然是。
“难道卖药的就不是人吗?那颗心一样也是肉做的呢”
男人们是金大班的恩客,也是她的劫数。
曾经的金大班想要一份奢侈的爱情,她嘲笑其他舞女捧棺材板,她“在抗争,一直不服命运的安排而堵上了二十年的青春,却输得一塌糊涂,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
她那么铭心刻骨的爱,她和朱凤一样有过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”的奋不顾身,但她的冒险,她的铭心刻骨换来的是什么?
是月如的“此生不复相见”,是一个又一个男人爬过她的肉体,是在花天酒地里佯装的真心与言不由衷的曲意逢迎。
于是,怀揣着梦想摸爬滚打守望了二十载,她是向命运低了头:
她最终嫁给陈发荣,这个年老、秃头、计较且家产不丰厚的老头,连一封信都不留给那个可怜巴巴拿着7万元存折要讨她“做老婆”的痴心大夫。
饶了一圈,带着一身伤痛和苦楚,又回到了男人身边,让男人主宰自己的命运。
这是命运对她的戏弄,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最深刻的反思与嘲讽?
白先勇先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。但我总觉得金大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失败者”。
不同于同为舞女的尹雪艳,尽管她们过去都是百乐门红极一时的舞女,都曾搅乱了人心,被认为是妖孽下凡,但是不同于活在别人口中的尹雪艳,金大班却倔强地拒绝被讲述,被描绘。
即使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,下嫁给陈发荣,金大班还是选择用自己的话将这典型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的烂俗故事讲给众人听,即使跌跤失败,即使输得一塌糊涂,她还是那个金大班,活得立立正正的金大班,认命却不服输,感慨身世却不惧未来的金大班!
“乐声起,歌声扬,耳边吴侬软语,乍暖还寒的夜,
红灯将灭酒将醒,曲终人散终一瞥,
谁能此时话离别?最后的一夜……”
所以,在夜巴黎的最后一夜,舞池里的她温柔、缱绻,她拥着那个脸红的少年,通过他望向二十年前的金兆丽,明天如何呢?是带着遗憾嫁人活成另一个任黛黛?还是保持着这份倔强,接着做梦,不服输的活下去?
没人知道,也无需知道……。
本文来自风信子投稿,不代表胡巴网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://www.hu85.com/366882.html
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邮件至 xxxxx@qq.com 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