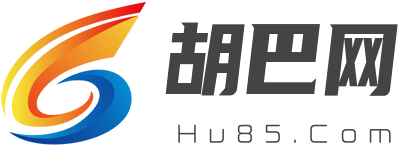借春节之际,回到了我的故乡。逗留半月有余,突然想起温州来,不知阳台上的仙人掌枯死了没有。这种想法越来越浓烈,便决定去温州看看。
清晨,很早便起来辞别了父亲,打算到城里去买车票。县城离我的村庄并不是太远,八九里路程又都是柏油路面,半个多小时便可到达,可我害怕独行。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同学,一个也不在。早不知道到哪里游玩去了。深冬的云南,风景是凄清的,一切庄稼都已经收获光了。经过学校的门口,也改换了名字和模样。先前供我们读书纳凉的叶子花树倒是还在,只是多余的枝叶被修剪去了。我感到生疏,没有多久,我的兴致早已索然,有些后悔此来为多事了。

寻不到同学一同前往,只得独自上车。公共车半个小时一发,等待的时间也是让人感到极为苦闷的。看着车窗外行人脚上各式各样的鞋子,似乎是这个小镇唯一的变化。乘客陆续上车,公共车缓缓启动。驶离了狭小阴湿的店面,那破旧的招牌都依旧的小镇。公路旁偶尔跳出一两株果树,树上被主人落下的几只秋橘格外显眼。我尽量把这一切记得深些,这一次出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这种宁静很快就被打断了,我的前座有一对男女在交谈。那女子满口粗话不绝于耳,似乎是在抱怨小镇的公共车太少,以至于她无法到达想去的地方。男的一直在安慰她,要她到县城转车到鸡足山去。此类环境引发而来的,是我越来越深的眉头。没有什么可以消遣的事情,便很自然的拿出手机,看着屏幕发呆。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车中的无聊。收获过了的土地里,枯黄的玉米杆随风摇曳着,飞快的从我身边闪过。我在国骂声中睡着了……
不知过了多久,司机师傅操着方言机械般地叫嚷着:“到站了,下车了。”乘客们不太情愿的走下车,似乎在埋怨司机吵醒了美梦。我向下客门走去,不经意的看到先前把国骂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女子有些像我的旧识。尽管如此,我并没有打招呼的意思。匆匆下了车,掏出手机翻了许久的电话本拨出老同学的号码,竟然接通了。我问她在福建还是云南。中学毕业之后她去福建,联系渐渐少了。经过确认,刚才的女子的确是我的旧同窗。我让她在车站等我,我一会就来。赶忙买好车票便去寻她,心里有些激动。学生时代我和她关系很好,算是红颜知己。竟料不到在这里意外地遇见老朋友——假如她现在还许我称她为朋友。那四处张望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。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,脸上也上了粉底。但一仔细看也就认识了,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迁缓,或许是庄重的贵族气质和高跟鞋之故。很不像当年的调皮淘气了。
“芷妍,是你么?我万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。”我还清楚的记得她的小名。
“屈功前,是你?我也万万想不到,你刚才为何不叫我?”
“我怕认错人,也没有和陌生人说话的习惯。”我答道。
她邀我同去鸡足山,原来她要去为她身在福建的母亲办身份证。多年未见,又因闲来无事,我便答应下来。细看她相貌,瓜子脸略显苍白,可能是化妆之故。然而哀瘦了,精神很沉静,迷人的大眼睛也失去精彩,全没有先前她国骂时的风韵。但当她缓缓地回顾的时候,却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美丽来。
“我们”我高兴地,然而颇不自然地说:“我们这一别,怕有六七年了罢。我早知道你在福建,可是实在懒得过分,终于没有打一个电话……”
“彼此都一样,我现在在泉州,已经四年多,和我妈一起。她回来接我的时候,知道你去了北京,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。”
之后彼此无语,或是无从说起。跟她一道的男子,这才走了过来,芷妍介绍道:“这是我老庚(老庚是云南结义兄弟的互相称呼),学校里就交的了,这次上鸡足山叫他做个伴。”
“你好”我说。
“嗯,你好”他缓缓答道。只见他一头棕红色的头发,左耳上挂了个手指大小的耳环。一件灰色的衬衫只扣了一个纽扣。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,脚踏一双人字拖。他从裤兜里掏出一盒卷烟,点上火叼在嘴里,递给我一支。
“我不会抽烟,谢谢。”我说。他也不客气,把烟放回烟盒便在我和芷妍的后座坐了下来。
“你在做什么?”我问芷妍。
“美容美体,在我妈介绍的朋友店里。”
“这之前呢?”我接着问道。
她借着车窗的反影捋了捋刘海“无非就是做了些乱七八糟的事,等于什么也没做。”她也问了我毕业之后的境况,我一面告诉她一个大概,一面叫售票员买票。我们之前原是不客气的,但此刻却推让起来。售票员并没有耐心看我们争抢买单。“三个人,四十五块”接过我的钱一边找零,一边对芷妍说:“下次你帮他买票不就得了?”我和芷妍争抢买票的时候,她老庚一直看着窗外,全无要客气一番的意思。
“我一回到老家,就觉得人生很没有意思。”她一边玩弄手指,似笑非笑的向我说。
“我在学校时,看到或是听到为了挣钱不惜绞尽脑汁的人们,就感觉实在是可笑,也可怜。可想不到现在我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拜金主义了。总也逃不出这个荒凉的地方。又料不到你也回来了,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?"
“这难说,大约也有思乡情结的人吧。”我也似笑非笑地说。“但是你为什么不写书了呢?”
“写书?”她的眼角闪起一丝光亮,很快又暗淡下去。“早就停笔了,挣不了几个钱,还不够我买化妆品,更不用说其他的了。”
公共车从花桥水库岸边驶过,阳光照耀着水面闪烁着点点白光,像晶莹的泪花。我略带些哀愁。
“我妈身份证到期了,她又不愿自己回来办理。这几年又总和我爸吵架,一点也不顺利。便让我顺道到鸡足山寺院里上上香。本来年前就打算回来的,可春运时期,农民工返乡。车太挤,车票又太贵。一直挨到现在乘着年假的空闲,我才得回云南拜佛。”
她拍了拍衣角并不存在的灰尘继续说道:“福建那边今年又下雪了,冷得要命。看我手指都长满冻疮了。”说着把红肿的手伸给我看。又觉得有些失礼赶忙缩了回去。“还是云南的气候好。”我说道。
“嗯,香我回来的那天就已经去上过了,身份证没有办到,只得今天再跑一趟。我实在是个庸人,我想不到也会对曾深感可笑的佛像跪拜。跪拜过后,福建应该不会那么冷了,我想。很多时候,看到你博客里那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了。在你的空间里也看到一些。好久没去读你的诗歌了,我还记得以前说要周游世界的梦想。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,敷敷衍衍,模模糊糊。”
“我很喜欢你写的那些文章。”我说。
“我现在连话都说不清楚."她向她老庚要了一支烟,点上火。
“看你的神情,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,我现在自然麻木很多了,但是有些事还看得出。这使我很感激。然而也使我害怕和不安。怕我无颜面对至少对我心怀好意的老同学。”她突然停住了,狠命的吸烟,不停地咳嗽。我心疼的拍了拍她后背“别抽太多烟了,对身体不好。”至始至终,她老庚安静的看着这一切。 她满脸已经通红,我微微地叹息,一时没话说。
她母亲的照片无效,身份证最终还是没办好。下午大家都有些饿了,找了一个小饭店,我几年前在这里吃过,味道不错。点了几个菜,但又无味,入口如嚼泥土。芷妍现在似乎不喜欢吃辣椒了,一直说太辣,不停地喝水。我与她老庚喝了些酒,也觉得苦涩无比。
“那么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?”
“以后?没有想过,学好美容美体,找一个不太冷的城市,开一家美容院吧。”
服务生送上账单,交给我,她也不像初见时候谦让了。眨着大眼睛,听凭我付了钱。
回程的时候,末班车已经走了。我包了辆面包车,她和司机讲起了价钱。黄昏时分,她和她老庚提前下车了。我住的地方稍远些,独自一人坐在车里。风还在刮着,从车窗挤过来,吹在我的脸上,倒觉得很凉爽。零丁的果树还是会偶尔跳入我的视线,而后又飞快的离我而去。夕阳洒在柏油路上,一切都像不曾发生过。
本文来自胡巴网投稿,不代表胡巴网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://www.hu85.com/136524.html
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邮件至 xxxxx@qq.com 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